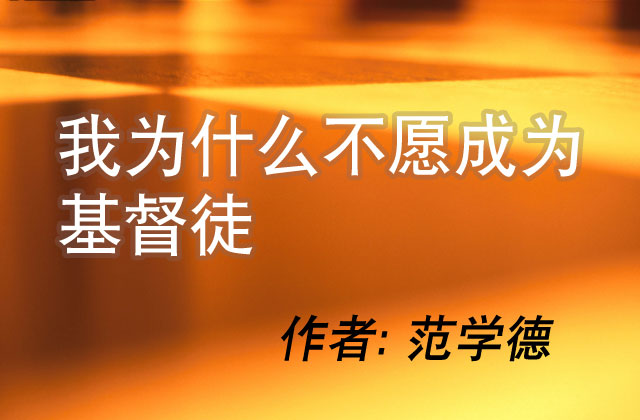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
范学德
以往,我很自负,自信能计画我的未来,如贝多芬所言,扼住命运的喉咙。我大学毕业后,立志成为一个学者,梦想写出一两部五百年后还有人读的立言之作。我的学术论文,得到了中央政府颁发的奖金。我的学术论著,被国家教育委员会评定为优秀图书,我为此而自豪,以为那就是我生命的价值所在。我把生命的意义等同于我的论著,把立言当做我的永恒,所以,我没有兴趣去寻求上帝。
在美国,我失去了自我。我所学的哲学专业,很难找到工作。能找到工作的学科,我没有兴趣学。著书立言成了过去,买菜、作饭、清理房间、照料孩子,成了日常生活。多少次,我一遍遍地问自己:我的永恒是什么?生命有什么意义?
我以为命运捉弄了自己:我没作过美国梦,却来到了美国。在美国,计画中的短期探亲,成了长期居留;被抛到了异国,却又偏要承认它是家园。我作不到!迷茫中我总是忘不了越剧〈红楼梦〉中宝玉的那句惊叹:「我在哪里哟!」为什么昔日的壮志雄心竟成了消逝了的梦,伤心的梦,怨恨的梦。我对未来曾充满信心,但今日,却觉得生命之路已到了尽头。当我走在我为自己设计的生命之路上,还能指望什么结局呢?那本是一条或长或短的绝路,路的尽头是死亡。如果人死了万事皆休,那我应料到,看到这条路的尽头,也不过是或早或晚的事。
可我心不甘哪!还不到四十岁,怎么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!但我不得不承认,我无路可走!美国不是我的家乡,可妻小都在这里;我年迈多病的老父老母,骨肉相连的兄弟姊妹,我的朋友,我的过去,都在中国,可中国在大洋的那一边。我的心被撕碎了。我下不了狠心,抛离妻小而重返故里。但生活在美国,对我如同在狱中,好像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我的理想、壮志、计画,都化为一缕缕轻烟,散入蓝天白云间。
难道我从此就该认命?为了维持这个家,勉强自己、委屈自己,把后半生消磨在怨恨和无聊之中。可我怎能情愿心甘!「天生我才必有用!」这诗句,曾激汤了我多少少年壮志。而今,人依旧、鬓未白、志已衰。天生我,所用何在?古人云:「哀莫大于心死。」我心既死,今后即使走在生之路上,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。
我绝望了。我不想成为现在的我,尽管我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;我成不了我理想中的我,尽管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。(注1)我只是从北京到了芝加哥,人依旧,却失去了我。多少次,我不断地问自己:我是谁?是我的理想、工作和社交生活?还是我的论文、论著和职称?如果它们代表了我,我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失落感?如果它们是身外之物,那我以往苦苦追求,它们意义何在?如果它们仅仅代表了我的过去,那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怎么竟分裂成了两个人?如果它们不代表我的过去,那么,什么构成了过去的我?我生命中那永恒的东西是什么哟?
我认识到我生命中那永恒的东西,是对永恒本身的渴望和追求。如果我已有了永恒,我不会绝望。我如此绝望,证明我苦苦追求的永恒不在我的生命中。如果永恒在我身外,那它是什么呢?(注2)
到哪里我才能找到那生命的永恒支点呢?那支点,它应坚如磐石,存于此刻,不变而支撑万有,历久而日日常新。但这磐石般的支点在哪里呢?也许,这支点就是死。人总有一死,确定无疑。与其在痛苦和怨恨中煎熬,何不早日了断。但这又谈何容易!我怎忍心孩儿失去慈父,白发人哭送黑发人。再说,死随时可以来临,无论它何时来临,都意味著我的毁灭,它不可能构成永恒的支点。
一九九四年那个圣诞夜,我从教堂回家后,还问自己:在美国还要待多久?我的路都已经被堵死了,还等待什么?我还有耐心熬下去吗?
感谢你,耶稣!不到半个月后,你就让我知道,我等待的就是你!在美国这三年多来我等待的是你!自我离开母腹后,我一直等待著的就是你!我等待著你的拯救。在我生死存亡的关头,你救了我。是你,应允了你的儿女们的祈祷,让我历尽波折后,来到了我不爱来的美国,从而不情愿地挣脱了成名这枷锁对我的束缚。戴著那枷锁,我眼睛只盯著地上那短暂的名声,不会寻找永恒;是你,剥去了一切令我自夸的东西,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的无能、无助和无奈。当我自信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,我不甘心把生命之舟的舵交给你;只是在绝望中,我才向苍天呼唤:上帝啊,你在哪里?
我越是证明上帝的存在,越是感到他离我而去;我越是否证上帝的存在,越是觉得他不断地干扰我,搅得我心烦意乱。
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这一天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获得了新生。
这一天的开始像平常一样平淡。把孩子送去托儿所后,我回到了家里,继续读韩客尔(Carl F· Henry)著的《神、启示、权威》一书。这部神学巨著的二、三卷,有八百多页,我已认真地读完了。手中正在看的第四卷,也读了一大半。
是什么力量引导我选择了这本书,并津津有味地读下来了呢?是天意吧。我通常愿意读在宗教观点上标新立异的著作。可韩客尔是二十世纪福音派的卫道大师,这几卷书是论述正统福音派信仰的大作,可它们却吸引了我。
我告诫自己,如果韩客尔不能说服我,今后,别人再想说服我就难了。韩的确是大手笔,他把福音的道理论述得头头是道。那深刻的见解,不断地打动了我的理智,使它获得了很大的满足。虽然我还是不信耶稣,但是这本书却处处把我推到了十字路口上:信,还是不信!我希望发现一个中间地带,不要这么非此即彼。可找不到。好像一种什么力量透过这书,处处逼我作出选择。我真烦恼极了!自己信不了,可又想尝到信仰的滋味。不想再啃这些神学书籍了。却又无法把它们放下。
几年来,我读过了许多有关基督教信仰的好书,它们再三地启迪了我的心灵。特别是福音书,几度撼动了我。我不承认耶稣是上帝之子,但我在英文作业中坦率地承认:耶稣是圣人。如果耶稣是中国人,如果耶稣不说他是神之子,我会毫不犹豫地说:耶稣是我一直寻找的恩师,在人之中,我愿永远与他为友。
可是,我无法理解,这个木匠的儿子,何以可能是上帝。独一真神、三位一体、道成肉身、神迹、复活等等,在这种种超理性的问题面前,我迷路了。我越从理性上理解这一切,问题越不可理解;我越是证明上帝的存在,越是感到他离我而去;我越是否证上帝的存在,越是觉得他不断地干扰我,搅得我心烦意乱。
我突然醒悟:如果我不信上帝,即使再读多少好书,仍然无法被说服,仍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。我的理智虽能一再看到柳暗花明,但转来转去,结局总是山穷水尽。我不要再糊涂了,我困惑的绝大多数问题,本身就不是人的理智能完全理解的,而是必须凭信心相信的。如果我想明白这些问题,却对耶稣没有信心,那岂不成了想学游泳,却永远不下水吗?信,还是不信,就这么简单。若是信,我生命的主人就是上帝。不然,上帝外在于我的生命,我所困惑的问题,将永远使我困惑。
信,还是不信?在信仰上,这始终是我必须面临的第一个,也是最后一个选择。
一个问题似乎想通了,可心中又钻出另一个问题:我还有好多其他问题没明白呢。是啊!是有许多问题没明白啊!可我又想:那又怎么样?问题总是会有的,但第一号的问题,永远是信还是不信。想等到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之后,再确定信仰,这不过是推脱之词罢了。我总能找到没明白的新问题,来推迟我作出抉择的时刻;我总会发现现有的证据是不充分的,无法使我完全信服上帝的存在。并且,再好的证据。也是别人的经历,即使对他们而言那十分真实,但对我来说,仍无法确证。因我没有那种经历。而那经历,是我理解并经历上帝的唯一途经。
我认识到,我若真想寻找那说服我,使我一生对上帝坚信不疑的证据,我必须与上帝建立绝对信赖的关系。我若不投入这绝对信赖上帝、顺从上帝、跟随上帝的关系中,我和上帝就是隔绝的。既与他隔绝,怎能找到上帝与我同在的证据呢?(注3)
我在屋内走来走去,不断地问自己:信,还是不信?在信仰上,这始终是我必须面临的第一个,也是最后一个选择。如果我选择不信上帝,即使上帝不存在,我也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净化我的心灵。但若有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,而我选择了不信他,那么,我不仅没有任何机会亲身经历到他,反而会失去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。
选择相信上帝又如何呢?如果我选择了相信上帝,而上帝并不存在,我的选择当然错了。但这错误的选择值不值得呢?值得。起码,这是一个高尚的选择。而且,它至少给了我一个唯一的机会,使我能确证没有上帝;而上帝若存在,这就变成了我亲身与他相遇的唯一可能,唯一机会。
这带点冒险的味道。我嘲笑自己。可作事能一点险也不冒吗?不信耶稣,我不也有冒险的感觉么。关键在于:这个险值不值得冒。人生充满了冒险,而最大的莫过于:我看不见上帝,但敢不敢信他。帕斯卡(Pascal)说得好:「如果我们把我们生命的赌注押在上帝存在这点上,并且,我们对了,那么,我们会赢得永恒的拯救;即便我们错了,我们输掉的也很少。反之,如果我们把我们生命的赌注押在没有上帝这点上,即便我们对了,我们赢得的很少;而如果我们错了,我们会失去永恒的幸福。因此,让我们权衡这两种机会:如果你赢了,你赢得了一切;如果你输了,你输得一无所有。押赌,然后,丢弃一切犹豫,承认上帝存在。」(注4)
既如此,还有什么好说的呢,我必须冒这个险。即便我错了,除了不作坏事外,我失掉的不过是些时间和金钱罢了。金钱本是身外之物,失去一些又何妨。这么看来,信上帝根本就没冒什么大险。而不信,才是最冒险的。因自己把赌注押在一无所有上,若输了,只能输得一无所有了。
我若把信仰推到明天,那么,信仰对于我就永远不会成为真的,而只是一个可能性。
好像我心中正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一样,就在我已下决心在信仰上来个跳跃时,又一个想法冒出来了:反正早信晚信也不在乎今天,算了吧,明天再说。
我又在骗自己了。我怎知我还有明天?信仰是关系我生死的头等大事,怎能拖到明天。此刻,我活著,清醒,有抉择能力,为什么不抓住机会,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立即抓在手呢?明天,万一我出了车祸,暴病身亡了,成植物人了,那么,今天岂不成了我的最后一天,而我却把它永久地丧失了吗?在面临确定的机会时,我犹豫不决,反而指望在机会极不确定的明天,再去抓它,这不是糊涂么。
再说,我的明天是什么?它只是一个可能的时间,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我活在今天,拥有此刻,这是实在的时间。正因我有今天,并且能思想,所以,我才有可能推论,如果今日之我延续下去,那么,它就可能化为明日之我。而这个明日之我所生活的时刻,对今日之我则构成了明天。
明天,不属于此刻的我。属于我的,是我当下拥有的此刻,以及此刻我对逝去了的今天的回忆,对向我走来的今天的计画。我此刻所计画的未来我的明天,它可能存在,也可能不存在,最终,必然不存在。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真实、确定的明天,但对我来说,明天仍然是不真实的、不确定的,是想像中的。我的明天会永远地消逝。我的明天,随时可能不存在。
明天它即使存在,也不是为我而存在。明天,日历上的那个明天属于公众,不可能被我垄断。我在日历上的某日上写的是:我要干什么事,而不是明天。我的明天和我要做什么密不可分,具有强烈的个体性,计画性。它的公式是:我想要……,我设想……,我计画……,明天是我的一个计画。
我要作什么事,是我未来的生命活动;而明天则是这一活动得以展开的一段历程。这两者都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,是此刻的我思。因此,我的明天不存在于明天,它存在于此刻,是此刻我对于我的未来的计画。
我所经历的时刻永远是此刻。在此刻,我向往、希望、计画。我在计画中把我化为一个可能性的存在:即在我将经历的时间历程中,我能变成什么。因此,虽然我不能确保我在下一时刻会实际地成为什么,但我能不断地规划我可能成为什么。所以,我若把信仰推到明天,那么,信仰对于我就永远不会成为真的,而只是一个可能性。既然为一可能性的存在,它就可能这样或那样存在,也可能不存在。换言之,我明天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:信,还是不信。
信不信耶稣,这心志的抉择,永远是在此刻发生的。
我继续分析明天与决志的关系:明天何其多也。今天拖明天,明天一觉醒来,还是今天。而那个今天之后,还有明天。明天将不断地后退,直至退到我不再能设想明天。因此,除非我把我的明天限定在某一天,不然,明天必然溜掉。而我若把我的明天限定在某年某月某日,那么,它就不是明天了,而是确定的一天。
但我并没把信耶稣定在某一天。我只是在逃避,拖延作出最后抉择的那个时刻。之所以如此,因我太相信自己了。即使在绝望中,我也只是对我所遇到的不顺心的事和物绝望,对不能成为我自己绝望,我从没对「我」绝望。但是,离开了上帝,我怎能成为我自己?我若不对依靠自己而成为我自己绝望,怎会投靠上帝。
信不信耶稣,这心志的抉择,永远是在此刻发生的。此刻,我信了,就是信了;不信,就是不信。有了,全有;没有,一无所有。属于上帝,就是与基督为友;不属于上帝,就是与基督为敌。
我把我的抉择推到明天,于是,在此刻,我还是不信。我若说「我明天信」,那是撒谎。因为「我明天信」这个信息,此刻存在于我脑中。它与我大脑中存在的「我今天不信」这个信息彼此矛盾,二者不可能共处。或者,由于我今天还不信,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能不能信;或者,我此刻决志信主了,那我就不必推到明天。
这时,我非常渴望我能有大勇气,不逃避耶稣多年来向我发出的挑战。把今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,去作出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。
我逼迫自己的良心如实地回答:我不需要拯救吗?我的良心能说不吗!问题只是:谁能救我?是自己吗?是妻子吗?是父母吗?是兄弟姐妹、亲朋好友吗?是集体、组织、政府、共产党吗?是那些冰冷冷的理念吗?都不是。若他们能拯救我,我早就被拯救了。但我沦落到如此地步,恰恰证明他们无力拯救我,即使他们有心。
我还能向谁呼救呢?我只有向耶稣呼救。我在绝望中向耶稣呼救。耶稣是我唯一的拯救!我求他以他的怜悯、慈爱拯救我。让我在他的爱中心灵得到安息。让我投入,消失在他的生命中,获得一个真我,一个永恒的我。
我认真地思考「神是永恒」对我作出信仰上的抉择的意义。我的结论是:只要我在时间范畴中思考上帝的存在,上帝总是先于我思而存在于此刻,并构成此刻之为此刻的决定性条件。上帝既然存在于此刻,那么,我与上帝相遇就不是与过去的上帝相遇,也不是与未来的上帝相遇,而是与此刻的上帝相遇。
与上帝在此刻相遇,我就是投入永恒:我有了过去,因为上帝创造了时间,我的现在与永恒的创造者相连;我也有了未来,因为上帝赐我以永生;我更有了现在,因我要跟从的是耶稣。
耶稣啊,在此刻我与你同行,就是行在永恒中。此刻与你同在,瞬间成为永恒。主啊,你使那个永恒的时刻快临到我了。那抉择就在一念之间。
耶稣基督为我准备了一条最好的路━━回家的路,它直接导致了我被基督所拯救。
这时,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,想找一个神学生谈谈。我想起了正在三一神学院读博士的吴弟兄。但就在几乎已经抓住了耶稣恩典的时候,我又动摇了。我突然决定不与吴弟兄分享我今天的特殊感觉。而是谈点深奥的问题,这问题是:圣经是无误的吗?圣经是上帝默示的吗!
我想起了几天前读的一本好书《认识主基督》,但我想从中找到有利于我的偏见的证据。我急忙翻开它。我的目光是多么恶毒!它只落在了这句话上,四福音书中关于空的坟墓的记载中「一些细节是有明显冲突之处的,有的不很重要(例如:妇女的数目,天使的数目,以及他们是坐著还是站著);有的就比较令人困惑,比如,如果耶稣的身体已经用香料膏过了〈约翰〉,而且坟墓被兵丁封守著〈马太〉,为什么妇女们还带了香料来膏耶稣呢〈马可与路加〉?」(注5)
匆匆地再看了一下四本福音书中关于耶稣复活的不同记载,我知道自己要拿什么问题向吴弟兄发难了:到底有几个妇女来看坟墓?她们在墓中看见了几个天使?天使是坐著还是站著?在不同的记载中,哪一个记载是真的?如果所有的记载都是真的,那岂不是自相矛盾?如果有一个记载不真,那么,圣经怎可能完全无误?
我在电话中向吴弟兄提出了我的难题。他解释说,这就好像不同的记者报导同一个现场事件一样,他们看的角度不同,记载的也不一样。我马上反驳,福音书的作者不是记者。如果圣经上的记载是神默示的,那么,它不可能相互矛盾;如果它们相互矛盾;它们就不可能是神的默示。在同一时刻,同一地点,如果在那儿是一个天使,就不可能是两个,而且,他(他们)不可能同时既站著,又坐著。
我想同他深入探讨一番,但又不愿把我今天的独特感受直接告诉他,怕他知道后抓住我不放。虚荣心不允许我给别人留下这个印象:即我是被人说服而信主的。于是我问他忙不忙,正巧,他很忙,我无法去他家与他继续争论。
当时我心中很失望。怎么他感觉不出今天对我有多么重要啊。现在才明白:是神阻止了我和吴弟兄继续争论。因为我们是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,并因此而受到一些理解对方的限制。我若见了他,还会为了争论而争论,不会只仰望神。迷途中的我,哪里知道耶稣的精心安排!又哪里料到,耶稣基督为我准备了一条最好的路回家的路,它直接导致了我被基督所拯救。
放下电话后心里很别扭,要与基督徒谈话的愿望非常强烈,好像不与他们说一说心话,我就活不下去了。真的,我是什么也干不下去了。
于是我打算找王峙军谈谈。他也是神学生,但我并不熟悉他。当著他的面,我曾把他妻子所作的见证,大大地奚落了一番。可我还想同他谈谈。拿起电话前,我在心里发誓,如果峙军也没时间同我谈,今后,谁也别想再与我探讨信仰了。当我打电话到峙军家时,他正在睡觉。但听我说要同他谈谈,他立即说,你马上来吧。我放下了电话,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仅仅几分钟前,心中的恶魔还搅得我焦躁不安,鼓动我否定圣经的权威性。可此刻,他的魔力哪里去了?是耶稣,驱散了遮盖我目光的滚滚乌云。是耶稣,降伏了在我心中兴风作浪的恶魔。
回想起来,一月九日这一天发生在我生命的这一切,太奇妙了!它处处展现了上帝的慈爱、智慧和精心安排。若不是上帝亲自干预,这一切怎可能发生!可我那有限的理智,无法明了神那深邃无边的睿智;但我的心,却分明感受到了神的 慈爱所带来的温暖、柔和、宁静。它在这不尽的爱中,卸下了压迫它的千斤重担。
慈爱的天父,感谢你,你使我看见了救我性命的真理:你是我生命的主。
在开车去峙军家的途中,在与峙军讨论问题的过程中,真理的光射入了我的心田。我明白了,我所斤斤计较的那些 问题,完全无关紧要!我是在那里钻牛角尖,是在逃避那生死攸关的真理,不敢面对真理向我发出的挑战。
这生死攸关的真理,向每一个灵魂发出了昀后的挑战:「神爱世人,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,叫一切信他的,不至灭亡,反得永生……信他的人,不被定罪;不信的人,罪已经定了,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」(约三16、18)
在这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上,四福音书完全一致,没有任何矛盾。四福音一致地记载:人们看见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,人们看见了埋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人们看见了复活了的基督一再向他们显现。
并且,四福音书和整个新约完全一致。所以,彼得才向犹太人这样宣讲,「这耶稣,神已经叫他复活了,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……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」(徒二32、36)所以,保罗才告诉弟兄们,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:第一,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,为我们的罪死了;而且埋葬了;又照圣经所说,第三天复活了;而且显给矶法看;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。」(林前十五3、4、5)所以,老约翰在信中才写道,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,就是我们所听见,所看见,亲眼看过,亲手摸过的……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,我们也看见过,现在又作见证,将原与父同在,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,传给你们。」(约壹一1、2)
并且,新约和旧约完全一致。它集中表现为:旧约中的关于弥赛亚的近二十个最重要的预言,都被耶稣应验了。读过〈以赛亚〉,谁能忘记五十二章和五十三章呢?
我心中对神有说不出的感谢。我说,慈爱的天父,感谢你,你使我看见了救我性命的真理:你是我生命的主。但是,我还是不明白许多问题,就连我向吴弟兄提出的问题,虽然,我思考了许久,但还不明白。但我相信,圣经的作者既然是在你的灵的感动下,写出的话语,那么,这些细节上的不同记载,必是你允许的。你既允许这些,那它就绝不是我接受你救恩的障碍。我在这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纠缠不休,那是我低著头不看你,所以,我看到的一切都成了我的绊脚石。任凭那些愿意自己被绊倒的人,绊倒在自己设下的绊脚石吧。主耶稣啊!我却要跟从你。在不懂的时候,我要保持沉默,只仰望你,思念你的救恩。我要从你的救恩中得到智慧和力量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,相信那最高真理:上帝使复活了,上帝称你为主为基督了。
主啊,我求你赐圣灵给我,让这真理的灵引导我,进入你的生命,使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中生长,长成你的生命。鉴察人心的主怜悯了我内心的软弱!看我像刚学走路的孩子,摇摇晃晃的走著,他亲手扶助了我,为我安排了又一条新路,奔向天家。
几个月前,我了解了德国神学家潘霍华(D· Bonhoeffer)的生平,这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,使我看到了伟大信仰所造就的伟大生命。在我和峙军弟兄谈了一段时间后,我们的话题引到了潘霍华身上。我们都景仰圣灵在潘的生命中所放射出的灿烂光华。就在这时,峙军告诉我,他愿把书架上潘霍华的英文版大作《门徒的代价》(他还没读呢!)借我拿回家看。
上帝啊,这是你为我准备好让我在今天读的书。我虽早就想了解这本书的基本观点,但却从来没到任何图书馆去借 这本书;而在我的心刚刚转向你,却还困惑在现代世界中怎样才能过基督徒生活时,你就让我读这本书。
我读过这书的头两章后,就决志作主的儿女了。
主啊!我相信,是你为我设计了这一个特殊的门,它是只等待我来敲的门,是我必须敲的门。
一月九日的晚上,我独自在书房中读《门徒的代价》。
潘霍华说:「廉价的恩典把恩典视为一套教条、一套原理、一种制度,它意味著宣称罪的赦免是个一般性的真理,上帝的爱被视为基督徒对神的一种概念。人们以为在知识上接受了这一套概念,就足以获得罪的赦免。在这样的教会里面,世界为其罪过找到了廉价的遮盖,无需为罪忧伤痛悔,也不必渴望真正地从罪中得到释放的。」(注6)
他又说:「廉价的恩典是宣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,受洗礼而不遵守教会的纪律,领圣餐而不必认罪,获得赦免而不需本人亲身忏悔。廉价的恩典是不需付出作门徒代价的恩典,是不背上十字架的恩典,是没有道成肉身的和永远活著的耶稣基督的恩典。」(注7)
读完这些话,我情不自禁地向上帝忏悔: 天父啊,请你饶恕我的背逆和愚昧。你以你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给我以救恩,可我却一直拒绝这恩典。请你允许我承认「我是罪人,我是一个不配得到你恩典的叛逆之子。」没有按照我的罪孽对待我,报应我。你的慈爱何等深远。
主啊,我感谢你的恩典。你的恩典是无价的珍宝,我愿以我全部生命作代价得到她。主啊,为了让我得到你的恩典,求你赐给我一颗新心,为我的罪而忧伤痛悔。让我无畏地面对我的罪,真诚地认罪忏悔。在实际生活中,实实在在地悔改,从罪的束缚中得到释放。
主啊,你不是概念,不是教条。你是此刻与我共在的神。你是永活的神,求你让我经历到你与我共在,求你在与我共在中,让我经历到你的生命。在你的爱中成为新人,在爱世人中学会爱你。
潘霍华说:「昂贵的恩典是必须再三寻找的福音,是必须祈求的礼物,是必须亲手敲的门。这样的恩典是昂贵的,因为呼召我们来跟从;并且,它是恩典,因为它呼召我们跟从耶稣基督。它是昂贵的,因为它叫一个人付出他的生命为代价;但它又是恩典,因为它赐给人那唯一真实的生命。它是昂贵的,因为它定罪;但它又是恩典,因为它使罪人称义。超越这一切,它之所以是昂贵的,因为它使上帝付出了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……昂贵的恩典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。」(注8)
我对耶稣说:
我的救主啊,我感谢你为我舍命。为了让我得到你那永恒的活生生的圣洁生命,在十字架上舍弃了你那最美好的生命。你既为我舍命,我这条命就属于你了。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,它本来就属于你。它今后只属于你了。我生命的主啊,求 你按照你的旨意,成就这属于你的生命吧。
主啊,求你帮我背上我的十字架。因那十字架是独一无二的,是你只为我预备的。若不背起它,我不可能看见十字架上的你,不可能理解十字架的真理,不可能传讲十字架的福音。十字架上的耶稣啊,让我背起十字架,跟随你。
潘霍华说,「唯有相信的人是顺从的;并且,也唯有顺从的人才相信……唯有信仰包含顺从时,才是真正的信仰,这绝对不能没有顺从。并且,唯有在顺从的行动中,然后,信仰才成为信仰。」(注9)
读完这段话后,我对真信仰的了解大大加深了。我默想:
主啊,尽管我现在还没在灵和真理中深刻地体认你,但是,从今晚起,我的心开始顺从你。我怀著一颗顺从的心相 信你。你使我明白了,相信你和顺从你、相信你和跟从你,是绝对不可分开的。相信你是信仰的起点,这是而且仅仅是逻辑上的起点。在时间的范畴中,在历史的顺序中,在实际生活中,相信你和敬畏你、顺从你,相信你与爱、跟从你,是不分先后,同时发生的。主啊,求你赐我信心,一颗敬畏你、爱你、顺从你的新心。
主啊,我来敲门了,我带著无限的悔恨敲门了,我带著无限的希望敲门了!主啊!我相信,是你为我设计了这一个特殊的门,它是只等待我来敲的门,是我必须敲的门。主啊,我来敲门了,因你爱我,怜恤我,愿意接待我这浪子;因我爱你,敬畏你,愿意作你的羔羊。主啊,你听到了我的敲门声了吗?请你开门,开门吧。
主啊,我要奉你的名祈祷。
附注:
- 1·祁克果对「致死的疾病是绝望」有精彩论述,「对自己绝望,绝望乃至于消除他自己,这是一切绝望的定式」。《祁克果的人生哲学》,第87页,基督教文艺出版社,1996年。
- 2·同上引「绝望正是由于丧失了永恒和自我。」第130页。
- 3·施莱马赫认为,宗教的本质存在于人之「绝对依赖的感觉」之中。参见李道生编著《世界神哲学家思想》,第265页,荣耀出版社,1992年。
- 4·帕斯卡(Pascal)语转引自希克斯(John H· Hicks)《宗教哲学》(Philosophy of Religion),第59页,Prentice-Hall,1990年。
- 5·法兰士(R· T· France),《认识主基督》,第166页,校园书房出版社,1990年。
- 6·潘霍华《The Cost of Discipleship》(中译本《追随基督》)引文自译,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, 第45~46页,1963年。
- 7·同上引,第47页。
- 8·同上引,第47~48页。
- 9·同上引,第69页。